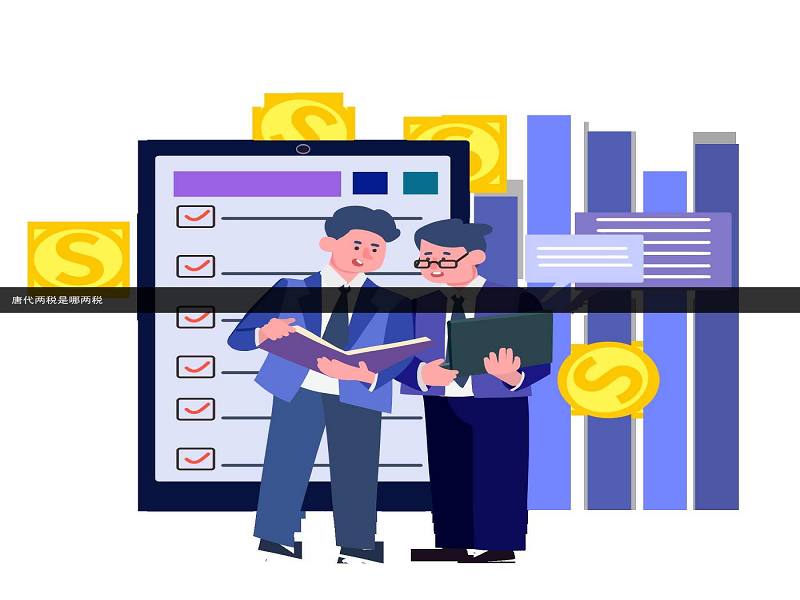
唐朝货币制度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空前辽阔,“前王不辞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唐大诏令集》)。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政局稳定,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实行和推广,使得农业兴旺,手工业发达,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及交通运输的发展。出现了杜甫《忆昔》诗中所描述的“公私仓廪俱丰实,男耕女织不相失”的繁荣景象。后期则因战乱不断,人口大量南迁,带动南方开发,并使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这一时期因均田制被破坏,赋税制度由租庸调制变更为两税法。货币税的兴起,既是铜钱地位提高的表现,同时也消弱了绢帛的货币地位,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因此,唐代的货币制度也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特点是钱帛兼行,绢帛所占比重似乎更大;后期铜钱开始居于主要地位,因钱荒而增强了白银的货币属性并出现了飞钱櫃坊。总体上讲,唐代是我国古代货币经济复兴和实物货币衰落的过渡时期。自东汉末年一直衰弊的商品货币经济,至此才又以新的面貌发展起来。唐代货币的流通,最广的是钱,其次是绢,银与金则又次之。
前期:高祖到玄宗(618-756)
唐朝前期的币制特点是钱帛兼行,但是绢帛似乎发挥了比铜钱更重要的货币职能,地位更为重要。绢帛自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曾长期发挥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几乎已成为十足的货币。唐初沿袭这一传统,特别是与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调制征收实物税,政府每年征收大量的绢帛,用以发放官员的俸禄、赏赐以及支付政府的大型活动开支,使绢帛发挥了支付手段或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补充了流通中金属铸币的不足以及大额的支付。唐初使用绢帛比使用铜钱数量多且范围广,后来铜钱所占比重逐渐加大。玄宗曾下诏要求不得专用铜钱,甚至规定铜钱使用限额,超过限额必须使用绢帛。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诏曰“自今以后,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罗丝绵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课罪”(《命钱物兼用敕》)。说明开元年间铜钱在流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地位日益上升。前期物价稳定,没有大幅度的跌宕起伏,其中开元通宝保持了稳定的币值及较强的购买力,应是成就开元盛世的重要条件之一。
后期:肃宗到昭宣帝(756-907)
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昭宣帝13朝,历时约150年,是唐朝由中衰到消亡的时期。政治上经安史之乱的打击,中央控制力减弱,藩镇割据势力形成。朝官与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朝官间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政治日趋腐败,黄巢起义更加速了崩溃的步伐;经济上因战乱的破坏,农业有所下降,但手工业及商业仍有发展。因均田制的破坏带来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由以征收实物税为主的租庸调制改为以征收货币税为主的两税法。在促进商品货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更给货币流通及货币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后期的币制特点是此前实行的钱帛兼行体制受到冲击,绢帛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铜钱开始居于主要地位,因此社会上对铜钱有持续的大量需求,但铸造量有限,遂出现了时间长达七八十年之久的钱重物轻的“钱荒”现象,给唐朝后期货币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白居易的《赠友诗》“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就表达了对钱荒和赋税征钱的不满。为解决“钱荒”的难题,唐朝政府推行了开放铜山、禁铸铜器、广铸铜钱、严禁毁钱为器、禁止私家蓄钱、限制铜钱外流、倡导兼用绢帛等措施,武宗时甚至采取了毁佛铸钱的极端手段,但始终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了维系帝国的正常运转,唐王朝解决缺钱危机的措施可谓花样百出。
第一,在缺钱的情况下,唐朝政府给官员的俸禄不是足额用钱支付。在早期,除了按照官员的品级给“职分田”,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津贴一部分来自“公廨田”的产出收入,《新唐书》中有记载,“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同时,为了使帝国官员能足额领俸禄,唐朝还由中央财政特地划拨一笔钱,称为“公廨本钱”——给中央各衙门和各级地方官府提供本金去做贸易、向百姓放贷,所得的利润、利息补贴衙门各项津贴费用,以及官员俸禄的不足部分。为了让公廨本钱获得高息,负责经营“公廨本钱”的捉钱令史绞尽脑汁,甚至逼迫百姓与之贸易借贷,“民不堪其扰”。其后,唐朝政府在官员俸禄上多有变革。
第二,政府要求富人必须消费。“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政府命令民间富人的钱都“放”到市面上,以缓解市面的“钱荒”。更甚者,在元和十二年(817年),为缓解京师地区市面钱荒,通货紧缩,不仅从国库拨出钱50万缗来购买京城市面的布帛,而且,严禁权贵富人家中积蓄实物铜钱,超过5000贯的处死,王公大臣则重重治罪,其资产“没入于官”,十分严厉。这一来,巨额铜钱不允许放在个人手上,京师富人赶紧消费,“乃争市第宅”,一下子将大唐京城的房价炒得很高。
唐文宗时期还曾明确规定:“(个人)积钱以七千缗为率”,超过七千缗,就得消费掉,并且限期消费,家有十万缗的在1年内消费掉,有二十万缗的以2年为期限,否则处罚。
第三,为了增加市面铜钱的供应量,在扩大开采铜矿,多采铜铸造货币的同时,唐朝政府还将主意打到了佛像上。政府一再严禁民间或寺庙将铜钱销毁用以铸造铜佛。大和三年(829年),政府规定:全国佛像材质用铅、锡、土、木建造,少数法器才允许用铜制造,否则处以极刑。到了唐武宗年间,政府打击佛寺,将所有的铜佛像以及钟、磬、炉、铎等铜器都收缴,这样为各地铸钱提供了大量铜材。于是,不仅中央可以铸造铜钱了,还允许各地官府开铸铜钱,“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
第四是唐朝政府控制铜器物价,稳定市场。贞元十年(794年),政府在下令禁止百姓铸造任何铜器的同时,还规定,民间铸造的铜器,每斤铜器售价“其值不得过百六十钱”,照此,1000钱有铜6斤多,即便熔铸铜器销售,价格不过960多钱,这就保证了6斤多铜器的售价在1000钱内,此外熔铸铜器还有其它开销,如此,商人毁钱铸器无利可图,稍稍缓解了民间销毁铜钱铸造铜器的情形。
第五是铸造大额货币。铜实在不够造钱用,唐朝曾经发行大额货币。乾元二年(759年),唐朝廷铸造“乾元重宝”,每枚当50枚“开元通宝”使用。大历年间,负责唐帝国的财政官员“判度支赵赞采连州白铜铸大钱,一当十,以权轻重”,但是,这些虚值大额货币的弊端是更加助推了物价上涨,造成民间负担过重,大受其害。
第六是为货币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唐代晚期很多地方官员为保证本地的正常流通,禁止铜钱离开本土到外县,这样一来,商贩无法正常做生意,于是“商贾皆绝”。没有货币流通,地方商业基本停滞。其后,政府实在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铜钱用于流通,但是又不能让民间贸易断绝,于是“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元和二年(807年)规定,做生意支付额度达1万钱以上者,必须混用布帛。
第七是降低铜钱的“含金量”。元和年间,因为唐王朝要镇压反叛,“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大臣皇甫镈出了个点子:在流通中的每缗(以1000钱为一串)钱取下20钱作为“垫陌钱”之外,再抽取50个钱上缴国度用作战争时期特殊军费,这样一来,每缗钱实际只有930钱,虽然仍称为1缗,但实际缩水7%了。一定程度上,这缓解了当时的困难,但是此后百姓在买米盐等生活用品时,也都学着样儿,自行抽取7—8个钱,“糴米盐百钱垫七八”,政府想禁止也禁止不住,干脆朝廷下诏书“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出于缺钱,政府不得不认可民间金融流通情形。唐朝末年,京师流通的铜钱,名为法定“一贯”实际只有850钱,缩水15%,而河南府地区的铜钱流通,缩水更是达到20%,充分反映了当时铜钱的紧缺状况。
尽管有唐一代出台了种种招术,但是市面一直是不同程度的缺铜钱状态,甚至缺到只允许民间造铜镜,这也是很奇葩的事。

两税法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两税法推出的背景
第一,以“均田制”为依托的租庸调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根基。推行“两税法”之前,唐朝一直实行的是租庸调制,可以说,这种制度成就了唐朝的鼎盛国力,但到了唐朝中期,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唐朝初年经过多年的战乱,闲置土地较多,男丁又少,于是国家就推行了均田制,按照人丁的数量授田,你只要接受了政府的田地,就要以实物的形式缴纳赋税,还要为国家义务劳动,这就是租庸调制。可是社会经济发展向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个别家庭出现经营不善,或者出现了变故,家中的田产就被逼无奈要变卖,但是税赋却是按照人丁收取的,你即使失去了土地,国家照样得找你要赋税,于是大量农民开始逃亡,土地兼并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恶性循环,均田制名存实亡。既然均田制都没有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就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
第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势严峻,各军阀不听朝廷命令,横征暴敛,中央财政几近枯竭。同时随着募兵制的推行,国家的财政支出数量大幅度增加,为了国防的需要,朝廷允许各个节度使在本地收取赋税,这种财权的放任给后世带来非常头疼的弊端。安史之乱后,藩镇做大之势已经难以遏制,唐德宗的许多敕令形同废纸,藩镇根本不执行。这么一来,很多藩镇的势力范围内中央根本就收不上来赋税,而割据者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味地横征暴敛,全国各地赋税征收一片混乱,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第三,唐德宗有意做一番事业,尤其对削藩颇有意向,可惜朝廷孱弱的实力不允许武力削藩,只有另辟蹊径,于是通过税制改革的办法也就成了一条比较温和的、行之有效的“削藩”之策。眼看着国家糜烂如此,连政令都难以统一,唐德宗有意削藩自强,可是国家刚刚经历大乱,元气大伤,想动兵革,实力也不允许,当时的国家财政困难到什么程度,看看《旧唐书》是怎么描写的:
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军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完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
如此窘迫的财力,还如何组建大军与藩镇军阀们一决雌雄?那么武力解决不了的事,也只有从文治上解决了,所以税费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治理方式。
“两税法”带来的积极意义
第一,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与藩镇相比,朝廷再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优势。原先的租庸调制,到了唐德宗时期,难以继续推行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人丁征税的模式无法维持中央财政赤字,租庸调制下富人是以人口数量来征税,穷人也是按照人口数量来征税,问题是很多富人本身就是贵族,享有税赋的豁免权,实际上是变相加重了穷人的负担,这种税法使征税的根基变得很不稳定,征收上来的税额也越来越少,朝廷自然就没钱。而两税法不同,是以财富多少来征税的,无论是贵族还是富人,都没有豁免权,这样,征税的对象从人转向了财富,朝廷的收入当然会大幅度增加。
第二,两税法推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往的税法,都是以实物的形式缴纳,程序还是非常繁琐的。两税法不同了,统一折算成钱,或者折算成布匹,如此一来,田赋也都需要进行货币交易,商品经济自然也就活跃起来了,而且缴纳赋税的程序也简化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第三,两税法实际上削弱了藩镇武力对抗的经济基础。既然各个地方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而中央又没有武力解决藩镇问题的能力,那么采取一些文治手段也就非常必要了,藩镇最令唐朝中央政权头疼的就是财政自主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随意征收赋税,有些藩镇甚至富过了中央。两税法推行后,无论是中央控制区还是藩镇控制区,一律都要按照此法执行,以往朝廷在藩镇控制区无法征税,如今藩镇的钱也被征收到了中央。中央的财力得到了加强,而藩镇的财力则逐渐得到了削弱。
“两税法”的弊端和危害
兴一利必生一弊,利弊往往是相伴而行的,“两税法”作为一种制度,自然也难逃自然法则。其实这种制度的弊端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货币交易,伤农而利商。古代的中国,向来以农为本,农耕民族以农业生产为根基的。可是两税法的推行后,农民上缴赋税必须都换成货币,而朝廷并没有推行配套的金融政策,这么一来,物价通缩,钱贵而物贱,农民缴纳的赋税,实际上大大超出了以往的数额。改革前,农民只受国家的盘剥,改革后,农民还要经历一层商人的盘剥,自然也就出现了伤农的恶果。
第二,资产审查制度没跟上,造成了“竭泽而渔”。“水无常形”,人的财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家庭,经营得好,家庭资产得到了很大的扩充,而有些家庭的资产却严重缩水。朝廷征税是以资产多少为依据的,但缺乏及时的资产审查制度,家庭资产扩充的人家还好一些,但资产缩水的人家却依然要按照原先的标准交税,恶性循环,由富转贫,不得不逃亡。这么一来,制度也就变成了恶政。
总体上来看,两税法虽然弊端丛生,但还是为唐朝的财政收入带来了转机,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能够续命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主导者杨炎,是一个出色的财政专家,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因得罪了太多人,最终被朝廷抛弃,惨死于前往海南的路上,令人唏嘘。


 沪ICP备2021008925号-29
沪ICP备2021008925号-29